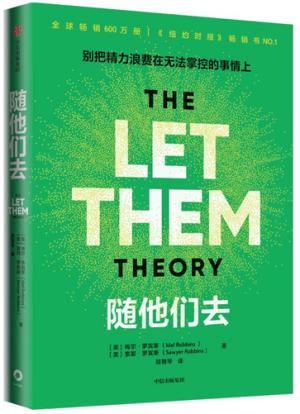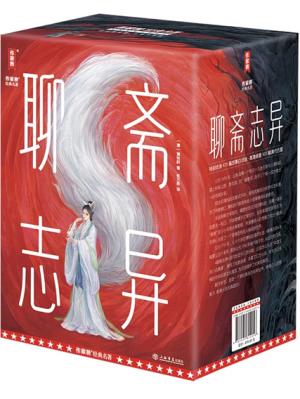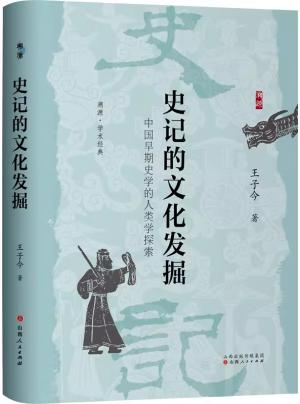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世界在前进
》
售價:HK$
81.4

《
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
》
售價:HK$
88.5

《
高句丽史
》
售價:HK$
1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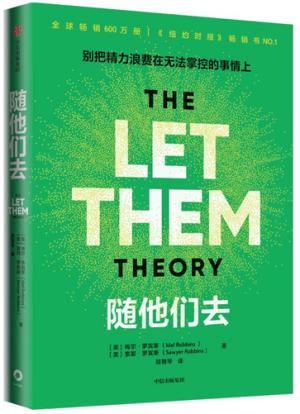
《
随他们去:别把精力浪费在无法掌控的事情上
》
售價:HK$
8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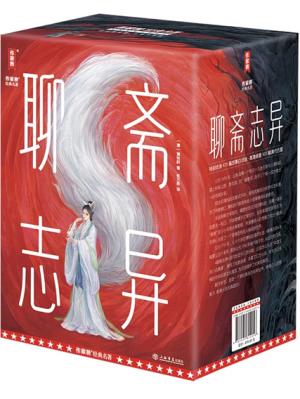
《
聊斋志异:2025全新插图珍藏白话版(全4册)
》
售價:HK$
5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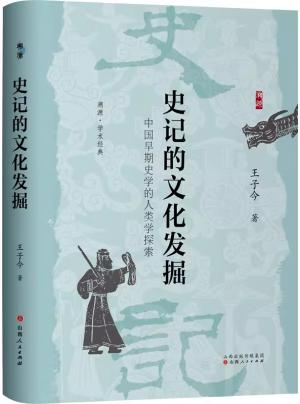
《
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
》
售價:HK$
199.4

《
风起红楼:百年讹缘探秘
》
售價:HK$
221.8

《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
》
售價:HK$
68.4
|
| 編輯推薦: |
1、文学大师多重角度解读文学经典
《聊斋》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但它也是一部社会寓言书、文化历史书、情感关系书、人性心理书。看文学大师梁晓声从多重角度为你解读这部包罗万象的经典名著。
2、阅尽社会百样情态,看破古今世相人心,提升读者思维层次
从清朝到现在,时空虽然早已转换,但中国式的社会关系,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却一脉相承。《聊斋》不仅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也足可以为我们现在的人所借鉴。梁晓声用他敏锐的目光,深厚的素养,为你挖掘《聊斋》中隐藏的社会规则和底层逻辑,提升你的思维层次。
3、看似狐言鬼语,实为醒世良言
梁晓声是一位翻译大师。只不过,他不是简单地将文言翻译成白话,而是将《聊斋》中那些“狐言鬼语”中深含的寓意为你翻译出来。你会发现,《聊斋》中的狐有狐品,鬼有鬼格,高于许多自以为人的人格。它们所说的话,句句都是醒世良言。
4、古今聊斋前后辉映,不可不读
本书后附梁晓声所著多篇仿聊斋式的现代小说。这些小说大异其趣,篇篇针砭时弊,扬善斥恶,直面现代人的社会关系、情感关系,深刻剖析现代人的人性心理,读后令人拍案叫绝!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解读《聊斋》的文化随笔。在本书中,作者对《聊斋》的文本特点、文学价值、人物性格、故事特色等进行了精彩评析,从《聊斋》隐喻的文字和内容线索中,寻找历史的草蛇灰线,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百样情态,捕捉描画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悲喜哀愁,以及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并从人性和道德的层面进行了深度挖掘。可以说是一部从微观视角切入,品评中国文化特点的极富意趣而又有人文关怀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另外本书后附有多篇作者创作的仿《聊斋》体的短篇小说,取名“聊斋新编”。与《聊斋》故事前后辉映,相映成趣。
|
| 關於作者: |
|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代知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创作了包括散文、小说、杂论、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逾千万字。代表作有《父母岁月》《雪城》《年轮》《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凭借作品《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
| 目錄:
|
上篇
梁晓声说聊斋
1?《聊斋》中的仁义与报恩 002
2?文言的精妙 014
3?我与《聊斋》 017
4?“怪力乱神” 019
5?当人性遇上道德 023
6?《聊斋》里的民间记忆 032
7?狐鬼爱情 042
8?蒲松龄的自我疗愈 048
9?美狐莲香 060
10?聂小倩、连琐与狐奶奶 070
11?《聊斋》中隐藏的历史真相 078
12?《红楼梦》人物的“狐性” 086
下篇
梁晓声聊斋新编
1?犬神 092
2?聂小倩别传 097
3?狐惩淫 100
4?异邦奇谈 102
5?怪猪 105
6?曲某 109
7?红磨房 113
8?鬼畜 118
9?死神 200
10?复仇的蚊子 208
11?咪娜 245
12?丢失的心 263
|
| 內容試閱:
|
1《聊斋》中的仁义与报恩
余喜读《聊斋》,自少年始。所读皆“小人书”,即连环画。当年,凡小人书铺,必有几本《聊斋》。亦有成套的,或曰系列的更为恰当——并未出全过,十几本却是有的。每页以中国传统的白描画法画之,那是最见线条功力的一种画法。印象中,每本都画得极细。画中人物,眉目俊雅,衣裙褶皱,简而有美感。
谈及《聊斋》,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画皮》。当年,我自然也是看过的,但从不认为是一个好故事。这乃因为,觉得故事的“主题思想”,显然是单向度针对男性的,而且首先是针对男青年的;无非就是告诫男青年,万不可被女性的外表美所迷惑,那是很危险的。因为,美女美的外表很可能仅仅是一张美人皮,其下包裹的是专吃好色之男人心的
厉鬼。
我们那时若学一篇新课文,老师必引导学生归纳“基本内容”,总结“主题思想”。故我们读什么课外书,也便养成了领悟“主题思想”的本能。
《画皮》的“主题思想”并不深刻,完全囿于一个大脑发育正常的少年的领悟力之内。
正因为我完全能够领悟,反倒极不喜欢,觉其单向度针对男性的“主题思想”对普遍的男性不啻是一种羞辱。
深层原因乃是,我既已为一少年,且属于相貌不俗之少年,对异性之美,遂日渐思慕,心颇好也。身处这样的年龄而喜欢《画皮》那样的故事,反倒是心理不太正常的少年了。
我当年喜欢的是《娇娜》《青凤》《婴宁》《聂小倩》《胡四姐》《莲香》《青梅》等爱情故事。在那些故事中,美女子非狐即鬼,然美而有仁义心。男子或“为人蕴藉,工诗”,或“静穆自喜”,或“狂放不羁”,或“性慷爽,廉隅自重”——总而言之,皆好男子,文学青年,还都属清寒之士。因无固定房产,每借宅而居,甚至栖身于旧庙荒寺,所以才有与那些狐姐鬼妹的艳遇。
以上故事中的爱情,有仁在焉,有义在焉;其仁其义,不仅体现于男之对女,亦体现于女之对男,互衔恩也,互报恩也。“知恩图报”四字,演绎得十分感人。于是,男女之爱具有了特别饱满的恩爱元素。
我们中国人说某一对夫妻感情深厚,常用“夫妻恩爱”加以形容。在现实生活中,夫妻之间真的一方对另一方有恩可言的例子是极少的,遑论互有恩德了,更遑论彼此欣赏,两情相悦了。非言“恩爱”,无非是共同生活久矣,互生体恤罢了。喜结良缘,便是相爱的男女之大幸了。对于绝大多数人,良缘也是谈不上的,所结只不过是婚姻,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人生任务的完成。
所以,少年时的我,爱读以上《聊斋》故事,乃因那类故事中的仁与义、恩与报恩是其他故事少有的,不仅使男女之间的爱情显得极为特殊,即使以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论,对我也具有莫大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那类故事中的仁与义、恩与报恩,对我后来的人性养成,确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比较一下,我们便会看出那类故事的不同:
《梁祝》是中国最出名的爱情故事之一。但不论梁山伯对于祝英台,还是祝英台对于梁山伯,其实都无恩可言。这个故事与其说令我们感动,毋宁说令我们同情。我们希望梁祝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果却不是那样——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强势外因的破坏,双双殉情而死,于是令我们心疼。化蝶固然是浪漫的、恒美的,但若问——有谁理解梁祝二人何以互相爱得那么深,八成许多人是回答不了的。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红楼梦》中的宝黛之爱。
不论红学家、准红学家们多么着力地为我们解读宝黛之爱的动人处,像我这种少年时期就很理性的人,却一向难以被感动。
我每听人言(多是女性)读《红楼梦》曾为宝黛之爱多番洒泪,便常起一种冲动,想要当面问:具体读的哪一章哪一段?愿读给我听听吗?
其实,很想获得一种分晓——看彼们是否会一边读一边哽咽。
虽然并没真的问过,却觉得彼们断不至于的。
我老老实实地交代,宝黛之爱从没感动过我。但我确乎是有点儿同情黛玉的——刚长成少女便失去了父母,从此寄住于外祖母家,爱上了表哥,却又明知爱不得,是以终日心有难言情愫而积郁成疾,以至于含悲早死。
说到底,不就是这么一档子事吗?
然莫忘了,其外祖母可是贾府的“老祖宗”,而贾府可是富甲一方的名府人家。她终日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一旦头疼脑热的,那么多人嘘寒问暖,除了爱不顺心遂愿,其他方面是不是可以说过的是很贵族的日子呢?
这么一想,我对她的同情就只能止于“有点儿”了,“多乎哉?不多也”。倘要求我对她的同情再多“点儿”,难。
有人说《红楼梦》是旷世伟大的爱情小说,我从没这么觉得过。我认为,《红楼梦》固然伟大,却并非伟大在爱情的内容方面。甚至认为,恰恰是对于宝黛之间的爱情,曹雪芹没表现出应有的想象力。我总觉得宝黛之爱缺一种或可曰之为“直教生死相许”的元素。因为缺,所以并不动人。
《牛郎织女》中是有仁、义与恩的元素在的。
牛郎被不仁的兄嫂以分家为名逐出家门时,仅要求将一头老牛分给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自幼放牧它,对它有感情了。
更因为,它老了,干不动太多太重的活了。如果自己不要它,兄嫂不会善待它,其命运必特悲惨。
牛郎在与老牛相依为命的岁月里,对老牛是特别爱护特别体恤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仁。
这是一个人对一头牛发乎本性的仁。
这一种仁,在中国古今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中写到的极少。
牛郎的仁,对于老牛是恩。所以,老牛在自知将不久于世时,嘱牛郎怎样怎样去偷一位织女的衣服;又在自己死前,嘱牛郎剥下死后的自己的皮妥善保存,以备应急时用。
我们都知道,王母娘娘遣天神将织女押回天庭时,牛郎带两个儿子可是乘着牛皮追上天的。至于没追上,终于还是被银河隔开了,那是神力强大的原因。我们只能替牛郎叹息,却丝毫也不能怪老牛百虑一失。
它只不过是一头老牛,它都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死后的皮贡献给有恩于自己的主人了,还要它怎样呢?
《牛郎织女》中的老牛,将义和“知恩图报”四字诠释到了极致。
我幼时第一次听母亲讲这个故事,确乎鼻子一酸流泪了。我的泪首先是为那头老牛而流的,其次是为牛郎和织女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将很难见到妈妈了——孩子总是更同情孩子的。
至于牛郎和织女之间的夫妻之爱遭到破坏,少年的我虽也同情,却比不上对于那老牛的敬爱深入内心。当然,主要因为我还是少年,难以感同身受地体会夫妻之爱的宝贵。
事实上,《牛郎织女》存在着一个人物关系的疑问,即织女对牛郎的爱究竟有几分是发乎真情的,又有几分是无可奈何的?
故事的情节是——若牛郎未偷走织女湖浴时脱下的衣裳,则她不会成为牛郎的妻子;因为没有那身仙衣,织女就回不到天庭。牛郎不但将她的仙衣秘藏了起来,后来还将它烧了,以使织女死心塌地做他的妻子。
如此看来,织女成为牛郎的妻子,当初肯定是无可奈何的。这不同于《天仙配》的人物关系。同样是天上的一位织女与人间的底层男子结为夫妻的故事,《天仙配》中的织女却表现为主动的一方:第一,她有思凡之心;第二,她已经在天上看得分明,董永不但是善良本分的人,且是大孝子,虽非什么“孝廉”,却具有孝廉品质,属于民间口碑承认的道德模范,令织女心生敬意。不消说,董永的容貌也是织女中意的类型。
那么,对于织女而言,下凡之前就已将董永锁定为自己的择偶之不二人选了。
正因为是这样,请槐为媒的情节才使我们看得会心。与织女会心了,由此乐见其成。董永与织女的关系,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关系。婚后之董永的幸福,必然先体现于织女的给予,后体现为互相的给予。在他们的夫妻关系中,不存在任何一方操控另一方去留自由的疑问。
这一类女方主动的爱情故事,在《聊斋》中举不胜举,占到一半以上。
故而,简直可以这样认为——一部《聊斋》,未尝不是中国最早的女子性解放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
像《牛郎织女》那类表现为男子主动的爱情故事,蒲松龄大抵皆以正面评价的文字为他们的人品作交代。由于他们基本属于正人君子,便对所爱女子负有无怨无悔的道德责任。《画皮》是个例,不在此论之内。像《莺莺传》中的张生那种“始乱之,终弃之”的男子,在《聊斋》中是很少的。
《白蛇传》就故事属性而言,与《聊斋》同属一宗。
《白蛇传》是有仁有义的爱情故事,也是女方主动的爱情故事。如上所言那种体现于男子身上的无怨无悔的道德责任,经由白素贞的行为传达得淋漓尽致,具有令人揪心的感染力。不论是为了救许仙之命而以有孕之身冒死去盗仙草,还是为了真爱与法海所进行的爱情保卫战,作为情节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特别是后一情节,每使我联想到《荷马史诗》中的赫克托尔。赫克托尔是特洛伊国王的长子,在十万大军直逼城邦之际,敌方的不败战将阿喀琉斯终日在城门前挑战的情况下,其迎战具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宿命的悲剧意味。因为他明白,对于自己,胜算几乎为零。他之迎战,既是为其王族存亡的迎战,也是为城邦荣誉所选择的殉身方式。
同样,白素贞迎战法海,也是明白最终的胜利根本不可能属于自己这一点的。她是为真爱而决一死战并且不惜殉身的。
故我一向认为,在中国一切形式的爱情故事中,《白蛇传》当列于经典榜首。
在罗马神话中,爱神和美神是一体的。小爱神丘比特是维纳斯的儿子。
中国没有公认的爱神和美神。
在绘画界,某些画家一厢情愿地将“山鬼”这一传说中的女性尊为美神,并画出了不少表现“山鬼”之美的画作。
那么,在中国,如果像评选一种国花般进行海选,哪一个爱情故事中的女性有可能被多数票选为爱神呢?
我要表明的是,即使反复选一百次,我的票也会一百次毫不犹豫地投在白素贞名下。这一文艺形象塑造得多么成功已无须赘言,还有另一原因在我看来尤其重要,即她的真身乃是一条巨蛇。
巨蛇啊!
自从人类有了编故事的能力,中国的《白蛇传》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它产生之前,蛇要么被视为图腾,要么是邪恶绝无丝毫人性可言的可怕之物。
蛇,而且巨,则不但可怕,简直还令人闻之色变,一见必定魂飞魄散。
将巨蛇变成的女子,塑造为不但令人必生大敬意而且令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人深受感动的形象,这种创作之念太超出人类想象的理性了。
或换一种说法,一个编故事的人的头脑是会极其本能地排斥此念的——因为像赫克托尔迎战阿喀琉斯一样成功率也几乎为零,不论其多么善于编故事。
成功率几乎为零之事,在我们中国获得了完美的成功——这使身为小说家且以虚构能力为职业能力的我,每一思及此点便会对古代同行卓越的想象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找不到北之感。
评价小说、戏剧以及电影电视剧的一个至今尚未过时的标准——是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或几个人物形象乃首要价值。
《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许仙、小青、法海四个人物形象,不仅皆成功,而且皆出色,各有各的性格光彩。
比之于《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之民间故事的经典性最牢固,不可撼动也,以至于不但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一再被搬上银幕,而且还被近年挺火的一首流行歌曲所唱。
就在此刻,邻家所放的音乐正传入我耳中——“法海你不懂爱……”
听来,不禁令我有穿越之感。
一个问题是——《牛郎织女》为什么越来越失去魅力了?
许多人肯定会这样回答——它在戏剧舞台和电影电视剧中再现的次数太少了。
那又是为什么呢?
乃因内容太简单了,简单得除了牛郎偷衣想要组成家庭和担着一双儿女乘着牛皮追织女追上天去两个情节具有故事性,此外再无任何具有故事性的情节可言。不似《天仙配》,虽然内容原本也很简单,但后人在原基础上加以丰富,使其内容足够一部电影。
每想,若《牛郎织女》是印度的民间故事会怎样?——大约彼们早已拍成电影了吧?印度电影载歌载舞的风格,必会使单薄的内容得到一定程度的充实。
若由好莱坞拍成电影,我推测,彼们必会在人与牛的关系上大做文章。
牛郎与兄嫂分家之前,兄嫂对老牛怎样,牛郎对老牛怎样,这无疑是有着很大想象空间的。
分家后,牛郎和老牛又是如何相依为命同甘共苦的,彼们肯定会想出生活化的好情节。
老牛教牛郎偷织女的衣裳这一原有情节,估计彼们会予以改变。这一原有情节有目的至上之嫌。虽然西方人中目的主义者也是不少的,但在文艺作品中,不顾当事一方愿意与否而以无礼方式达到目的之人,实际上便有了不可爱之处。以大多数西方人包括儿童的眼看来,牛郎靠偷正在湖浴的织女的衣裳使她回不了天庭而不得不成了他妻子的行为,显然是不可取的,甚至可能被认为是不光彩的。
彼们会怎么改呢?
偏偏那位织女的衣裳不知被鹰或猴子带到哪里去了,牛郎出于善意将不知所措的织女请回了家,并表示愿意为她寻找衣裳,而且真心诚意地带她四处寻找过,并终于找到了。
牛郎这么做,得到了老牛的支持。
织女恰恰是在牛郎将她的衣裳给她后,决定留下做他的妻子。这时的她,不但爱上了牛郎,对老牛也深怀敬意了。
后来呢,当牛郎和织女有了孩子,老牛成了他们的孩子最信任的朋友,孩子也从老牛身上学到了某些做人的原则和生活的常识。
如果《牛郎织女》在中国有着以上一种内容较丰富的版本,那么可以肯定这个故事的命运便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边缘化,甚至有可能成为当今的孩子们爱听爱读的故事。
从本源上说,《牛郎织女》是成年人为成年人所编的故事,目的在于给底层的男人们一种精神慰藉。当现实命运太清寒,与神女结为夫妻遂成为底层男人们的想象。但此种想象伴随着焦虑,目的主义的色彩就难免会掺杂进故事里。
中国人对牲畜一向缺乏西方人那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爱心。中国人即使爱它们,也往往是视为大宗财物来爱的。若对它们发狠,则完全没有什么罪恶感。
所以,尽管《牛郎织女》的故事中明明有一头非比寻常的老牛存在,千百年来我们也就是任它在那故事中仅仅作为一个使故事能够编下去的因素而存在,并不曾多赋予它点儿更文学化、人性化的意义。
如果《牛郎织女》中的那头老牛被赋予了较为感人的文学化、人性化的意义,则它将会成为全世界一切故事中最令人敬爱的一头牛。
迄今为止,全世界的一切古今故事中还没有一头令人敬爱的牛的形象出现过。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当代一位保加利亚作家写的《老牛》的确打动过我的心灵,但那是一篇散文,非故事。
前边提到了“神女”,与之有关的民间故事是《劈山救母》——一位书生,不知怎么迷路了,闯入了二郎神的妹妹的人间领地。神女由敬佩书生的才华进而爱上了他,而他也对神女一见钟情进而倾心。于是,相敬相爱、心心相印的二人在神女的洞府中结为夫妻,并有了一子。二郎神知晓后,觉得有辱神祇尊严,前来拆散。其妹当然不依,于是兄妹二人大战于华山,最终其妹不敌二郎神的法力被压在巨石下……
这个故事是文人为与自己同样在仕途上无望的同类而编的。文人们在仕途上无望,在爱情方面便也难遂心愿。文人们也需要以想象来自我慰藉,而这种情况下男主人公一向是书生。
之所以提到《劈山救母》,乃因此故事与《白蛇传》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后者中的女子是蛇精变的,列于妖册;而前者中的女子被尊为山神,列于神册。二郎神像法海一样,充当的同样是“替天行道”的角色,并都甚为强势,法力无边。二郎神的妹妹,则像极了白素贞,骨子里也有赫克托尔那么一股子“不战胜,毋宁死”般视死如归的劲头,为了维护自己的真爱敢于拼命。这个故事由于最终导致了亲兄妹之间的反目成仇、殊死较量,故也给少年时期的我留下深刻记忆。
在我这儿,以民间故事而论,《劈山救母》是当列于爱情故事经典第二的好故事。
《白蛇传》也罢,《劈山救母》也罢,若其一为蒲松龄所编,那么《聊斋》的文学价值当比现在高出许多;若都为他所编,那么蒲松龄与冯梦龙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方面的成就则难分轩轾矣。所谓“三言”,百二十篇中,流传最广的无非《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篇。
不同的是,“三言”是白话小说,《聊斋》是文言小说;“三言”中的小说多为编选,而《聊斋》中凡能曰之为小说的,则大抵是蒲松龄的原创。蒲松龄虽然承认自己能完成《聊斋》,亦赖“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但通读过后定会有此印象——凡“以邮筒相寄”的,大抵是那些没什么文学价值的民间流言罢了。
由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冯梦龙的贡献在于编选润色,蒲松龄的成就体现为创作。打着广泛征集的幌子进行创作,未尝不是一种自保稳妥的策略。
冯梦龙乃明人,蒲松龄是清人。
明人而以白话整理“古今传奇”,清人却以文言写狐鬼故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估计是欲证明自己的文学才华吧。
须知,蒲松龄青年时期即有文名,曾被视为地方才子,却非考场宠儿,始终没考上过举人。只是秀才而始终考不上举人,乃是在人前备觉羞愧之事。他差不多是一辈子当私塾先生,一生郁郁不得志。《聊斋》中《嘉平公子》一篇,讲该公子“风仪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试。偶过许娼之门,见内有二八丽人,因目注之”,故而与冒充娼妓名叫温姬的狐女发生了男女关系。
然此狐女非一般貌美之狐女,极富文采。伊与公子在床笫亲爱之际,“听窗外雨声不止,遂吟曰:‘凄风冷雨满江城。’求公子续之。公子辞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风雅,使妾清兴消矣!’因劝肄习,公子诺之。”
但是,这位公子委实只不过是腹中空空、徒有其表的“小鲜肉”而已。提笔落墨,满纸错别字,如将“椒”写成“菽”,“姜”写成“江”,“可恨”写成“可浪”。
美狐女终于难忍其学浅薄,批语纸上:“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荐。不图虚有其表!以貌取人,毋乃为天下笑乎!”言已而没。
对于徒有其表的世家公子哥,这样的讽刺足够辛辣了。蒲松龄还嫌温吞,又借“异史氏”之口评曰:“温姬可儿!翩翩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遂至悔不如娼,则妻妾羞泣矣。”——意思是,温姬呀可爱的人儿,他乃是世家之翩翩公子,你还计较他腹中有没有文才干什么呢?你这么要求,使他妻妾的脸往哪儿搁呢?
嘉平公子是《聊斋》故事中唯一一个“有幸”与狐鬼美女发生过亲爱关系,却因胸无点墨而遭弃的男子。与《莺莺传》刚好相反,“始乱之,终弃之”的不但是女方,而且是美狐女。
由此可见,蒲松龄的怀才不遇之心结是多么块垒难消了,在明人冯梦龙的白话小说流传广泛的情况下,作为后人而偏以文言写小说,以证明文言功底的扎实,这一种有意为之也就大可理解了。
蒲氏之恃才自傲,确乎有其不菲资本。且看他的自序,与同是清代文人的他者的评序相比,辞藻之旖旎绚丽,显居上乘,大有唐宋行文之考究,且不乏《离骚》《橘颂》之遗风: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
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
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嗟呼!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字里行间,作者之清贫生涯,亦跃然纸上矣。
我尤爱最后几句中“寒雀”“秋虫”之比拟,“抱树无温”“偎栏自热”的形容,读来令人愀然不复有语。
顺带一笔,1990年代,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在国内出版,有评论者奉为“真爱宝典”“爱情大全”。
那小说我看过,拍成的电影也看过;小说真的一般般,电影简直可以说很平庸。
若以“真爱宝典”“爱情大全”溢美之,窃以为《聊斋》倒是担得起几分的。用民间话说,可谓“五花八门”,以文学评论术语言之,便是“林林总总”“多姿多彩”,“各有其悲,各有其仁,各有其义,各美其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