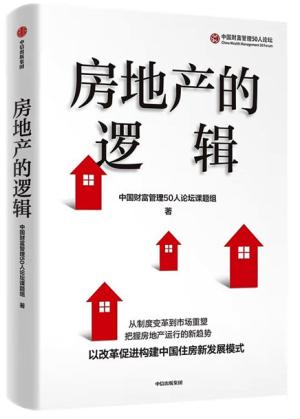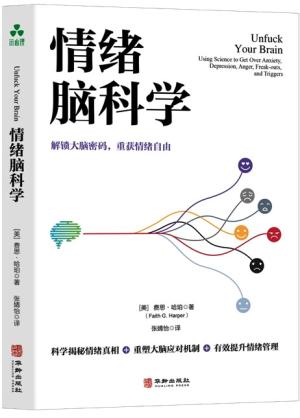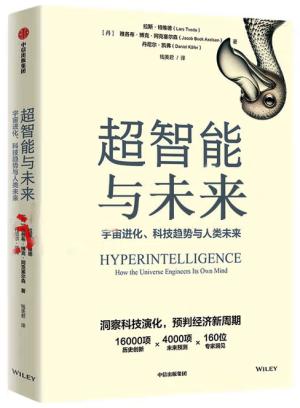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幻灭与觉醒:1861年的内乱、外交与政局
》
售價:HK$
96.8

《
文明等级论的表与里
》
售價:HK$
85.8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适用评释(修订版)
》
售價:HK$
2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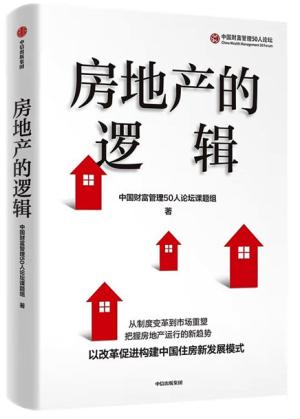
《
房地产的逻辑
》
售價:HK$
75.9

《
拉贝日记(全新版本。)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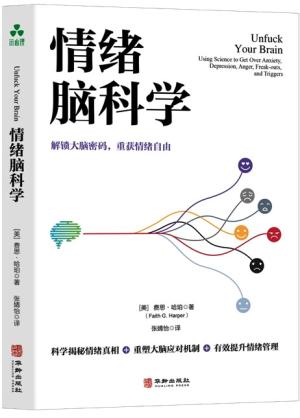
《
情绪脑科学 :解锁大脑密码,重获情绪自由
》
售價:HK$
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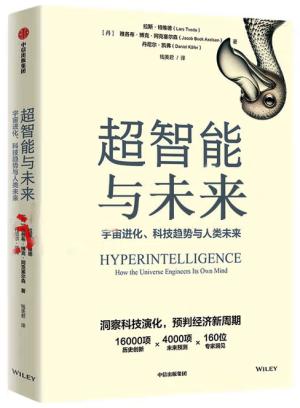
《
超智能与未来:宇宙进化、科技趋势与人类未来
》
售價:HK$
85.8

《
人比AI凶(“中国好书”“文津图书奖”得主万维钢全新力作;当AI无所不能,你靠什么不可替代?答案就在这里!)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英国首位女外科教授的不凡医学人生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终身成就奖、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获得者埃夫丽尔·曼斯菲尔德的回忆录
★开拓性女性的非凡故事
★女性的榜样
|
| 內容簡介: |
埃夫丽尔·曼斯菲尔德在20世纪70年代初获得外科医生资格时,确立了自己在各个意义上的先驱地位。当时,她的同事中只有2%是女性,当她告诉别人她的工作时,人们往往会感到惊讶,甚至感到怀疑和可笑。在8岁便怀揣外科医生梦想的埃夫丽尔,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完全胜任这一角色。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埃夫丽尔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医学界和社会已经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变化,但正如她通过自己的经历所展示的那样,女性要在其中找到自己
的位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 關於作者: |
[英]埃夫丽尔·曼斯菲尔德 Averil Mansfield
开拓性的外科教授。埃夫丽尔·曼斯菲尔德于1937年出生在英国布莱克浦,在那里的一所廉租房里长大。她在8岁便立志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1972年,埃夫丽尔不仅实现了职业理想,还成为英国首位女血管外科医生,后又晋升为英国首位女外科教授。其卓越成就为她赢得众多荣誉,1999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2018年荣获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终身成就奖。
|
| 目錄:
|
第一章
童年 ... 001
第二章
中学 ... 026
第三章
利物浦 ... 043
第四章
医生生涯 ... 079
第五章
外科女性 ... 095
第六章
培训结束 ... 128
第七章
顾问医生初体验 ... 149
第八章
杰克出现在我生命里 ... 168
第九章
圣玛丽医院 ... 196
第十章
何谓教授? ... 233
第十一章
放缓脚步 ... 259
第十二章
退休生活 ... 276
致 谢 ... 320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童年
1928年,我的父母在布莱克浦相遇。我的妈妈奥利芙·阿特金森兄弟姐妹四人,老家在阿克灵顿。我姥爷是名消防员。我的爸爸拉尔夫·德林兄弟姐妹六人。爸爸在赫尔出生,小时候搬家到威尔士,和他的爸爸一起在高尔为全家人建起了定居之所。德林家勉强可以糊口。我爸爸曾在曼布尔斯一带推车卖鱼,20世纪20年代时工作机会少之又少,他就从斯旺西一路来到布莱克浦寻求机会。
奥利芙和拉尔夫都在游乐海滩(Pleasure Beach)找到了工作,也正是在那里,二人相遇了。拉尔夫负责维修工作,奥利芙是收银员。两人会沿着海滨人行道漫步,偶尔去看电影,感情慢慢升温。虽然二人相处时间不长,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想要陪伴彼此共度余生。我姥爷并不同意两人的婚事,毕竟准新郎当时每周只能挣到二英镑十先令。不过两人还是勇往直前,在我妈妈21岁生日当天结了婚——年满21岁,就不再需要我姥爷的点头认可了。何况爸爸当时每周的工资又降低了5先令,想让姥爷点头同意他们的婚事更是难上加难。爸妈两人除了自行决定结婚,也没有其他选择。好在时间很快抚平了嫌隙。虽然日子有时过得紧巴巴,但父母一直恩爱有加,直到爸爸72岁离世,两人携手走过了将近50年时光。
妈妈和她的一位好闺蜜,还有我的一位婶婶差不多同时结婚,三人都希望结婚之后很快就能迎接新的小生命。然而,事与愿违。不过,五年后,她们三位竟然同时怀孕,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20世纪30年代,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尚未建立。妈妈发现自己怀孕几周之后,找到了库普医生,完全是因为库普医生是位女性全科医生。库普医生负责安排好了生产地点和产检事宜,主要包括血压检查和体检。妈妈到了孕晚期阶段,医生已经能够用胎儿听诊器听到胎心。但当时还没有发明出超声检查,也就无法看到胎儿的样子。
库普医生身材娇小,但是坚韧不拔,工作也确实要求她必须如此。妈妈分娩持续了差不多48个小时,最后只能到一家私人产科医院采取产钳分娩。我出生时重约4.73千克,算是“重量级”宝宝。妈妈由于难产必须接受手术,而且被告知不能再生孩子。颇为意外的是,手术之后,妈妈又患上了危及生命的肺栓塞(静脉血栓会从心脏流入肺部)——妈妈的这个经历日后成了我家的家传故事。爸爸被叫到医院,得知妻子正处在生死边缘。医生叮嘱妈妈不能活动,以免出现新的致命栓塞。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让小小的我甚是着迷。这或许能够解释我成为医生之后的首次研究课题为何是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
在我出生的1937年,医学界对血栓形成的原因、预防和治疗知之甚少,约等于无。但是,血液循环的原理已经一清二楚:心脏把血液输送到动脉,借助腓肠肌的收缩,血液再通过静脉,重新回到心脏。如果腿部静脉中形成血栓,血栓会进入肺动脉,形成肺栓塞,因此医生会建议静养。腿部静脉血栓大部分会在腿部静脉中留存、“重组”,也就是身体尝试重新打开已堵塞的静脉。但这个“重组”过程本身会引发身体深静脉的长期问题,导致血液回流到心脏的效率降低。不过这并不致命,所以完全卧床休息是当时治疗栓塞的首选方法,事实上也是唯一的方法。
让人开心的是,妈妈挺过来了,产后手术也很成功。不过,她不能再生孩子了。虽然我是独生女,但从不感到孤独。父母两边都有一大家子亲戚,大家住得很近,我从小就有堂(表)兄弟姐妹做伴。
那时的人们,对外面的广阔世界没有多少恐惧之感,在街上玩耍也不过是生活里平常不过的事。那个时候街上几乎没有车子,我整天和亲戚家的兄弟姐妹还有其他孩子混在一起。比起陌生人,我们更害怕的是踩到路面上的石头缝里。我们玩得最多的是球,当然也有其他游戏,比如用粉笔在铺路石上做标记,配上一串复杂的动作,有时还会边唱边玩。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是“跳房子”的各种变形玩法。大家都有跳绳,我们真的是一刻都停不下来,玩法层出不穷。所以,当时根本不用担心会得肥胖症。
我两岁时,家里搬到了布莱克浦莱顿地区的一处市建住房。尽管我对搬家那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但对搬家之前的事情却没有丝毫记忆,大概是新家的冲击和印象实在太过深刻。我清楚记得客厅的样子,还有哈罗德叔叔和埃尔西婶婶一大家人帮我们搬家的每一个细节。尤其是厨房通往后院的那段台阶,对我而言,那段台阶就是心之所向的自由之路。我记得自己当时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顺利上下那段很陡的台阶。最后我趴在台阶上,跪着滑了下来。
我们的新家在文布利路11号,是一栋把角的半独立式平房,一共两间卧室,还有一个很大的阁楼,它后来成了我的卧室。我们搬进去的那年,“二战”爆发了。
搬家之后的一大变化就是,我能一觉睡到天亮了,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个睡不安稳的孩子。据说搬进新家不久,爸爸就让我坐在地上粉刷自己的卧室,还在我身下仔细铺好了报纸。他确信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房间有了掌控感,我才开始好好睡觉。
爸爸烟不离手,抽烟是他唯一的奢侈享受。我想象不出他手里没有夹着香烟的样子。妈妈从不吸烟,她对爸爸抽烟的容忍,放在今天实难想象,但在当时,这样的情况稀松平常。我小时候久咳不愈,去看过很多专家,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这是常伴我左右的烟雾所致。我从小就在烟雾缭绕中长大,家里、车里,二手烟无处不在。
我家客厅里生着煤火,旁边连着炉子,利用煤火的热量进行烘烤。整栋房子只有这一个热源,因此有煤火的客厅也就成了全家的活动中心。每天睡觉前,我的床单、被子都会挂在煤火周围烤暖,趁着热气还没散去,赶紧铺回床上,可能还会外加一个热水瓶。不过,烧煤的烟气对我的咳嗽没有好处。
那时没有冰箱,杂货店又近在咫尺,从我家就能看见,所以妈妈都是每天采购当天所需。她要准备一日三餐,洗洗涮涮,虽然没有任何家用电器,但依然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有固定的配额,因此通常可以吃到蔬菜。爸爸吃素,我和妈妈两个人会额外补充一些蛋白质。爸爸很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屠宰场,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吃肉了;吃素在那个年代非常罕见。但是爸爸会吃鱼,有机会的时候,也能充当一下渔民。
我们搬到布莱克浦的时候,爸爸已经是氧乙炔焊工和切割工了。虽然这项工作很难,但它属于免征兵役工种,因此爸爸没有被征召入伍。我们小时候,身边的男人总是一个又一个地离开,那时的我们对此震惊不已。而我是幸运的那个孩子。爸爸看到那么多同胞纷纷奔赴战场,而他因为职业的关系留在后方,为此深感内疚。但我觉得他能在家里陪我,真是妙不可言。爸爸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6点,只有周日休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工作,风雨无阻,工作条件非常恶劣,但肯定比入伍要强得多。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拆除布莱克浦的摩天轮。工人们在毫无安全措施的情况下,顶风冒雨进行高空作业。但这是工作,更何况工作机会还那么稀少。摩天轮拆除工作完成后,爸爸在家附近塔尔伯特路的废金属回收站找了份工作。我只能想象爸爸他们在回收站干活儿时可能会骂骂咧咧,即便真是这样,他在家也绝不会出言不逊。其实,我小时候根本没听过有人说脏话。爸爸一直是我最好的榜样,所以我即使顶着巨大的手术压力,也不会说半个脏字。家里也很少讨论私人问题,除了一些感叹词,有好多词我根本没有听过。比如,后来教给我所谓的“生活常识”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含糊其词,结果我想知道的问题反而更多了。一般来说,生育话题似乎不太受欢迎,想来这是他们有意为之的小把戏,以防我意外怀孕。
爸爸的工资是按周结算,他总是将其装在一个棕色的信封里拿回家,由妈妈负责打开信封,分配钱的用途。妈妈会给爸爸一些零用钱,剩下的钱分别放进壁炉台上的几个罐子里,各有所用,比如用来看医生、买煤、付电费、交房租等。当时的工人阶层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是如此,确保生活开支足够,不会背上债务。债务,是工人家庭的大忌,他们会闻“劳动救济所”色变。像妈妈的手术费用这种额外支出会让一个家庭雪上加霜。
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需要打电话就去街上安全岛那里的红色邮政电话亭,用里面的黑色电话。从我家就能看到那个电话亭。偶尔需要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会看准时机,等没有人排队的时候马上出门。打电话需要投币,如果没有接通,按一下按钮B,硬币就会原封不动地退回来。我们小时候只要路过电话亭,就一定会去按一下按钮B,但只是“偶尔暴富”。
“二战”期间,爸爸除了白天的工作,还担任了我们这里的消防员。他利用自己的金属焊接切割技术,做了一台绝妙的灭火器,放在我家大门外,以备街坊邻里不时之需。蹊跷的是,虽然灭火器熬过了整个“二战”,却在战争一结束就不翼而飞了,我们再也没见过它。爸爸凭借焊接技术做的另一件杰作是我的滑板车。流线型的车身金红相间,绝对承载了我所有的骄傲和快乐。除了上学期间,我和我的滑板车形影不离。
|
|